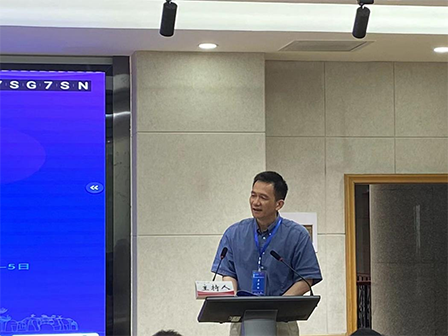英式教育让人终身受益
人物 · 2015-10-14 00:00
返回10月12日,亚当·斯密的同乡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因对消费、贫困与福利问题的研究,摘取了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现年69岁的迪顿,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Dwight D. Eisenhower讲座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是一位多产的经济学家,...

10月12日,亚当·斯密的同乡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因对消费、贫困与福利问题的研究,摘取了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现年69岁的迪顿,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Dwight D. Eisenhower讲座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是一位多产的经济学家,截至目前发表了80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5本著作。
安格斯·迪顿,1945年生于英国爱丁堡, 1967年获得剑桥大学学士,1971年获得剑桥大学硕士,1974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1983年离开英国到普林斯顿大学时,他已经因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而享有盛誉。早年在英国的教育,对他后来从事经济学研究有何特殊含义?2013年10月,他在接受《剑桥学子》(The Cambridge Student)专访时,回顾了早年在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学院求学的经历,并在点评了英式教育的优越之处。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经济金融网组织翻译了这篇文章,以飨读者。
专访新科诺奖得主安格斯·迪顿
作者:Aliya Ram 编译:董金鹏
1《剑桥学子》:您对计量经济学的兴趣源于何处? 安格斯·迪顿:在剑桥大学的头两年,我是数学专业的学生,对分析性的知识有一种天生的爱好。第一年的学士学位考试中,我对经济学的考试有些担心,所以选了许多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课程。虽然选了这些课,但客气一点讲,它们并没有开启我的学术生命。
《剑桥学子》:什么意思?那您的学术生命又始于何处呢?
安格斯·迪顿:如果你回过头,看一看1965年剑桥大学的教员,就全明白了。当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等人都在这里任教。你要知道,这些人对世界面临的贫困与发展问题可是非常感兴趣的。
《剑桥学子》:在您自传的结尾处,您写到了“困惑和悖论”,认为剑桥真正塑造了您的学术事业,是这样的吗?
安格斯·迪顿:是的。在美国,传统的经济学不重视分配问题,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但在英国情况就不同了,剑桥传统会告诉你:必须非常重视分配问题。
《剑桥学子》:您认为计量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有何交集?它们如何应用到公共政策中呢?
安格斯·迪顿:计量经济学是关于测量和统计的学科,而测量和统计也是任何有理可循政策的基础。除此之外,发展政策对评估有着极大的兴趣,而提到政策评估,计量经济学就有很多话要说了。

英国剑桥大学
《剑桥学子》:毕业后,您还回过剑桥大学吗?
安格斯·迪顿:从1969年到1976年,我在母校做了七年的研究员。此外,我还在马歇尔讲座发表过演讲,担任菲茨威廉学院的荣誉研究员。所以说,我还是不时回来的。
《剑桥学子》:这么多年,您扑捉到了什么变化?怎么看今天的剑桥经济学家?
安格斯·迪顿:上世纪60年代之前,经济学的重心在英国,但后来就转移到了美国,我认为这是很大的变化。毫无疑问,剑桥大学是非常适合学习的地方。我想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或许依然是经济学研究的重镇。在这方面,你可能比我更清楚。
《剑桥学子》:实际上,我不在乎大众对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的评价,但很在乎学术界对这里的看法。您认为,英国的大学如何鼓励非主流思想的发展?
安格斯·迪顿:我认为,仅仅用美国一流大学的标准定义一个院系的好坏,可能并不是一件十分明智的事情。但话又说回来,要避免这么做是十分艰难的。实际上,我认为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在内的美国顶尖大学,都是非常优秀的,但那不是经济学唯一的发展道路。我不清楚,剑桥大学的治理结构怎么让她摆脱美国的发展方式。对我来说,成长在一个更异端的环境中是非常宝贵的。虽然我不同意他们的一些观点,但他们的确对我的思想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剑桥学子》:您认为哪个国家的氛围更有利于您的兴趣和发展?
安格斯·迪顿:我承认美国和英国有非常大的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各自内部就整齐划一。比如,生活在普林斯顿就跟德克萨斯有很大的差别。
《剑桥学子》:我想,不同社会应该有相通的东西吧?
安格斯·迪顿:是的。学术研究的环境是跟其本身挂钩的。
《剑桥学子》:您好像读了很多东西,您的演讲和出版物中总是提及文学。文学对您来说有多重要?
安格斯·迪顿:英国教育有一点经常被人称颂,它要求学生在多个领域保持广泛阅读,而非狭隘地局限于自己专注的领域。文学和历史被认为对每个人都十分重要,当然经济学家也不例外。
《剑桥学子》:对您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是?
安格斯·迪顿:我不知道,因为我读了太多的东西。我读过很多医学领域健康方面的东西,于是我后来对健康话题非常感兴趣。此外,我还对事物间的组合感兴趣。总体上来说,我的书都涉及健康和收入,以及它们在人类福祉中的相互作用。
有两个人的著作对我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第一位是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我在剑桥的导师约翰·斯通(Richard Stone);另外一位是在剑桥待了一些年,然后又回到美国的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教授。
《剑桥学子》:一个对您的研究一无所知的人,他想知道您最重要的研究,您会告诉他什么?
安格斯·迪顿:每当有人问我,我做过的研究中最喜欢的是哪一项,我总是说下一个。但现在,我或许可以推荐下刚刚面世的新书,《逃离不平等》。对想了解我研究的人而言,它将是一个良好的开始。部分原因在于,这本书不含任何技术分析,书中没有方程,只有一些图表。尽管这本书意在召唤大众,但它同样值得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认真阅读。
《剑桥学子》:还有哪些内容,是您想谈但未谈及的?
安格斯·迪顿:我非常珍爱自己在剑桥的时光,我曾放弃了成为数学家的努力,最终发现经济学可能更适合我。在那些日子里,我扫遍了所有可能的知识和学问,后来还改变了专业,这是非常困难的。
我的两个孩子Adam 和Rebecca,都上过普林斯顿大学,我认为他们有更丰富和更广泛的教育,同时又没有丧失专业上的深度。
《剑桥学子》: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时,如何在知识广博和专业精深之间合理协调?
安格斯·迪顿:在某种程度上,这的确是个困境。对我来说,广博的知识来自菲茨威廉学院而非剑桥大学。在广泛的议题中培养你终身的兴趣,这正是菲茨威廉学院了不起的地方。
《剑桥学子》:能否用一两句话说说,您在剑桥的时候为什么不喜欢数学?
安格斯·迪顿:总体上来说,也不是不喜欢吧。我于1964年到剑桥的时候,课堂内容贫乏且陈旧,有时候甚至到了不可理解的地步。因此许多课程都需要菲茨威廉学院来监督,但菲茨威廉学院当时也不是非常强。此外,到这里攻读数学变成了购买时间做其他事情。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逐渐清晰的认识到自己并不想成为一位数学家。但我在那里学习的数学,使我以后受益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