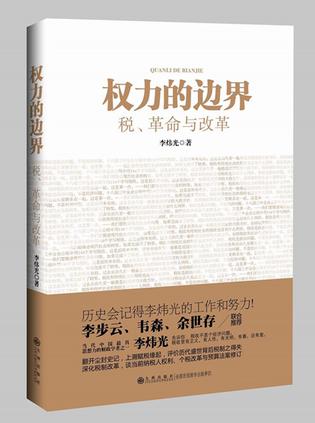今年6月15日,是英国《大宪章》签订800周年,世界上许多国家举行了纪念活动。英国的公共文化机构将这个日子确认为10大纪念日之一,还专门发行了纪念硬币和邮票,伊丽莎白女王和卡梅伦首相则出席了在宪章签署地兰尼米德举办的盛大典礼。在我们国内,民间也零零星星地举办了一些纪念性的研讨会。这确实是一个值得人们永远铭记的日子,因为人类社会自那个时刻起接近现代文明。从我所从事的专业意义上来说,它也是公共财政思想的发端。
大宪章宣布了一个人类文明史上的最重要的原则:未经允许,国王不得擅自征税。该原则强调,除传统捐税外,任何税收都必须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同意”。在当时,“一致同意”是指以大贵族为核心的大会议的同意,但“一国之主”征税还需要别人的同意,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现代国家的宪政民主,从此蒙生。
大宪章使得人民在法理的意义上获得了“被协商权”,它宣布有关立法、征税的事宜,都“应与全国人民普遍协商”。其中第14条规定:国王应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召集大贵族和有关人员协商,召集令需阐明会议的理由,于40天之前发出。王权专制大厦从此被撼动了,这是因为专制的灵魂,从来都是“说一不二”、“不可商量”的。根据这个原则,国王必须按时召开由贵族成员组成的、有固定场所的专门会议,这便是议会的起源。果然,数十年后议会便产生了,百年后,骑士和市民走进议会,下议院诞生。
关于国民的人身自由,《大宪章》声明:未经合法裁决和审判,“不得将任何人逮捕监禁,不得剥夺其财产,不得宣布其不受法律保护,不得处死,不得施加任何折磨”。为保证宪章的实施,将成立一个由25名男爵组成的常设委员会,用来监督国王和大臣们的行为。若发现国王有违反宪章的行为,委员会有权要求国王在40天内改正;若国王置之不理,委员会有权号召全国人民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发动战争夺取国王城堡,没收他的财产,而逼迫其改过自新。
人们都说《大宪章》的第61条最重要,就是因为其中规定了国民反抗暴政的权利。大宪章力求在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尽量用非暴力的而非公开叛变的方式达到政治目的。它仍将暴力手段列为选项,但只是将其作为一种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存在。贵族反抗国王权利的合法化,意义不亚于国王征税权受限之原则的确立,因为它为后世人民反对暴政提供了合法依据。这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极权思维形成天壤之别。
丘吉尔说:“宪章从头到尾给人一种暗示:这个文件是个法律,它居于国王之上,连国王也不得违反。大宪章的伟大成就,是它在普通的宪章中体现并重申了一项崇高的法律。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人们对它的尊重是有理由的。”他说,这种王在法下、法律至上的思想在历史的演变中逐渐升华成为一种国家建构的学说,“在后来的各个时代,当国家由于权力膨胀企图践踏人民的自由与权利的时候,人民就是根据这种学说一次又一次地发出自己的呼声,而且每次都取得了胜利。”(《英语国家史略》)
当然,受时代的局限,大宪章只是重申了国王的权限范围和贵族的封建权利,因而它不过是一份封建性质的文件和习惯法文献,但其具有的价值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其深远影响力一直达于今日。
20年前的时候,我没读过布坎南,不知道公共选择理论和宪政经济学;也没读过威尔达夫斯基,不知道政治才是国家预算的第一属性,但我在财政史的教学中接触过大宪章,它便是我最早的公共财政学知识的启蒙教材。从大宪章的那些似懂非懂的条款中,我知道了什么是王在法下、毋同意不纳税和“被协商权”。1998年,我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公共财政学论文《论公共财政的历史使命》,这一年中国官方正式宣布要建构公共财政体制。在这以前,中国的财政学是不加“公共”二字的,“国家分配轮”是它的主流价值,政府与市场、社会及公民个人之间的界限不在它研究的范围之内。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遗产一直到现在仍然影响着这个少有变化的领域,我们从现今财政改革的僵化和迟滞就可以看出来。
老子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是以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征税的无孔不入和不受限制的趋势,已经引起民间越来越大的不安和反感,此情此景与历代百姓对赋税的态度并无两样,都是税负过重引起的必然反弹。有关部门即使拿出相关法规来证明这种行为有所依据,人们还是不大买账,因为重税课征原本就与百姓“过小日子”的天理人情不合,也与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正常发挥相悖。比如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中有“收入畸高”并相应课征高税的处置方法,就是对企业家创新和居民提升消费需求颇为不利的一种规定。如何在企业和居民的自由发展与政府征税之间划定一条楚河汉界,是财政学一直关注不够的问题。
税收的功能不能仅限于征收数额的最大化,还在于如何体现公平正义原则。在税收正义问题上,人们比较认可罗尔斯第二正义原则,即不平等只有在有利于贫困者的时候才能被接受,即最不利者必须有所得益。而哈耶克的社会福利安全保障设施,其建立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公正或更多的福利,而是为人们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相比之下,后者更能体现古典自由主义精神。我们的税收研究,还远远没有达到正义的层面上,而缺乏公平正义的税收,无论政府多么需要,也不具备征收的合理性。比如,社会对富人承担社会公平的责任提出要求,富人也能接受这种要求,但税重到什么程度才相对于穷人来说是接近于公平的?还有,富人交的税,能通过政府之手去救济穷人、改善社会底层的生活状态吗?事实上,中国的富人和穷人一样,都对政府税收能否公平使用充满疑惑。
依照大宪章的经验,一个现代国家在设置它的“元”规则时,首先要在税收和预算上着力,用立宪的方式,给政府财政权力预设法律边界。政府之手必须保持干净,保持利益中性,并诉诸“知情权”来接受公民的审查。在现代社会中,财政是国家的,属于全体人民所有,而不能简单地称之为政府的财政。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体,权力分立、制衡和监督机制,新闻与言论的表达自由和与此相适配的财政信息披露机制,这三大原理构成政府合法性的来源。这是福山的“强有力政府、法治和问责制”的政治三要素理论的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实际应用,其中每一个要素都与财政直接相关。这就是我们把财政当做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原因,在这个前提下,才可以进一步追求公平、正义和效率的问题。
政府征税,首先要承认和尊重私人财产权在税收之先原则。关注私人财产权与税收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财产权利归属先定是消除矛盾、化解纠纷的要求,其它事情都应该排在它的后面。这一点中国古人认识得很清楚。《慎子•佚文》曰:“一兔走街,百人追之,分未定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但是在我国当下,物权法与税法的衔接得并不好,这个问题在未来数年间的不动产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直接税开征或改革中会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大宪章被称为现代国家预算的制度渊源,所以预算本质上应该定位于一国的政治问题。政治是预算的高层次问题,而它的技术和工具设计问题则是预算的低层次问题。天下没有纯技术或纯工具性的预算改革,所有的预算改革都具有政治意义。正如爱伦•鲁宾(Irene S. Rubin)指出的:“公共预算是政治过程的中心,它可以被用来帮助理解一个社会中的更广泛的政治过程。”(《公共预算中的政治:收入与支出,借贷与平衡》当然,并不是说低层次问题就不重要。美国1787年宪法,宪政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直到进步时代的1921年颁布《预算与会计法》,建立起联邦和州的预算体制,美国的现代国家转型才算完成。美国的经验表明,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有了代议制民主还不够,还必须建立起现代预算制度。
财政学家认为,预算具有改变一个国家筹集、分配和使用资金的方式的作用,从而也可改变这个国家的治理结构,甚至可以改变它的公共生活,塑造出一种特定的国家与人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卡恩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只有在现代预算制度之下才可能出现,因而可以在实质上改变这个国家本身。这个思想也同样来自于中国北宋时代的王安石。他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这是一种“治国以理财为核心”的理财思想,极有现代治理意识。荆公思维太过超前,即使现在,国人依然不能完全读懂他。
这个认识很重要。我们推进预算改革,一直以为它是个经济问题,将预算法称之为“经济宪法”,只认识到它属于政府内部的改革和治理问题。其实,我们正在推行的预算制度改革,已经在推进中国迟滞已久的的政治体制改革。收支测算和国库进出的背后是,谁获益了,谁支付了成本,博弈过程是怎样的,会导致什么后果,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
现在财政体制改革越来越强调预算和财政信息的公开透明问题,这也是大宪章精神的体现。大宪章之后,国王一步步地失掉了征税权和预算权,到最后王室的财产占有数额也都由下院作出决议才具有合法性。这里体现的法治精神极其重要:公有财产本该透明,详尽交代用处,拿出自己两袖清风的证明,遮遮掩掩,不许别人过问,绝对是不义的行为。其实不止是公共财产信息,从事公务活动的人员的个人财产信息也应在透明之列,阻隔、遮蔽、贪污公共信息的行为,亦为窃,应与经济违法同罪。
预算作为政府运作过程的基本规则,在认识上还有不少误区需要澄清。比如,人大批准的不是“钱”或“财政经费”,而是法律对各行政机构和政策项目的支出要求,即“预算授权”(budget authority);而得到预算授权也并不意味着就可以直接从国库得到可供花销的资金,而是意味着该部门从这天起必须承担起法律所确定的某种公共服务的责任(obligation)。2014年人大通过的新预算法和正在拟定中的预算法实施条例,在如何处理预算的立法者——人大和预算的执行者——政府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即授权与施政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之间的关系上仍存在很多问题,给未来的预算制度改革埋下不少伏笔。这些问题比较多地体现在它直接涉及的四个方面的权力和责任关系,即人大、政府、银行(指政策性的央行)和公众,不确定因素还很多,财税法治化进程任重道远。
熊彼特说过,财政是分析社会问题的最佳出发点,特别是在体制行将崩溃、新体蜕茧而出的“社会转型期”,尤其如此。他的话印证了大宪章在历史紧要关头所起的作用具有怎样的引导性。当一个社会陷入整体性危机、急需改革的时候,不能以财政收入的增长为目标和将其作为财税工作的重点,而是要把所有的问题——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都列为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解决方案。熊彼特说,只有使用这种特定的、与传统财政学迥然不同的方法从事研究才能奏效。熊彼特所说的这种综合性极强的方法,就是我最近以来十分感兴趣的财政社会学。这门学问在我国才刚刚兴起,知道的人还不多,不过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多的。
本书收录的论文和评论文章,是我本人对近年来我国财政制度改革和立法、修法过程中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成果,价值是大宪章式的,知识来源不止西方,也受中国道家和儒家的启发,而思路方法则是财政社会学式的。谨作为一种尝试,就教于同仁,也真诚听取读者的批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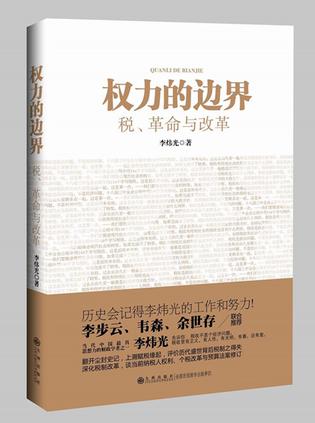
书名:《权力的边界:税、革命与改革》
作者:李炜光 著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年10月
书号:978-7-5108-3358-8
定价:4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