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日作家李长声先生6月17日19:00—21:00将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423教室讲茶道与日本文化,不能到现场的读者可以移步“腾讯直播”,观看“从茶道看日本”这场读书会。
耦耕读书会介绍
“耦耕”意为两人协同劳作的耕作方法,在我国的农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农为国本,供养的是我们的肉身,而读书治学,供养的则是我们的灵魂。清代诗人袁枚曾言“读书不知味,不如束高阁;蠢鱼尔何如,终日食糟粕”,书中百味,饕餮盛宴,值得莘莘学子细细品尝。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立志培养未来世界高端金融人才,“耦耕读书会”也就应运而生。“耦耕读书会”由腾讯·大家与经济金融网、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MBA项目联合主办,旨在营造读书的氛围,并提供思想碰撞的平台。在耦耕读书会,我们通过嘉宾与师生的互动,探索书中一个个精彩纷呈的世界,“耦耕”也就不再仅仅是协同劳作,而是“我们一起读书”。
耦耕读书会目前已成功举办两期,后续会继续邀请更多知名作家与读者零距离对话,持续推出一系列精品读书活动。
(可通过以下链接报名: http://www.hdb.com/party/vwvpu)
在读书会开始前,我们准备了十个问题,先问问李长声先生:

提问:我看最近流行的一个帖子,《日本文学11本必读书》,是您推荐的。请问:先生平时阅读,中文和日文占的比例如何?
李长声:平时在日本讨生活,几乎只阅读日文。读中文有一点休闲性质,上网翻阅。按住了键,流水一般地过目。而且,读评论多于读原书,往往读了评论也就不想找原书来读了。可说是读书甚不求解。我是1988年去日本的,被“开放”出去了,却没有亲身经历“改革”,所以落后于中国时代,不喜欢那些与时俱进的网络语言、饭局语言,没心情往下读,往下听,喝酒吧。
提问:您曾经写过,日本人很少藏书的,买了,看过,卖掉。您平常是怎么收集自己要读的书的?
李长声:日本流行过全集热,各种各样的全集,日本文学全集、外国文学、思想全集什么的,让作家们先富起来。不管是不是当摆设,家家的榻榻米上都立个书架,摆上一套两套的。后来经济发展了,1956年,也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那一年,日本宣布战败的复兴年代过去了,生活中流行“三种神器”(黑白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可居家像兔子窝,只好把全集卖废纸。有一个作家叫出久根达郎,当年他开旧书店的时候,拿一卷手纸换一套几十卷的全集。日本人爱读书,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舍书取电器者也。我爱书,见了好书也很想据为己有,但是在日本不大买书,一是因为穷,如今也不富,看见国人来日本大把大把地掏钱买书,真有点羡慕嫉妒恨;二是图书馆太便利,住家附近的图书馆藏书百万册,想读的都读不过来,哪里还有时间逛书店。而且,读书不是赶时髦,我又用不着急用先学,在书店里看到新书也耐心等到图书馆入藏了再借来读。当然,有些书时过境迁也就不读了,甚而庆幸当初没浪费时间。

提问:您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为国内媒体写日本文化的随笔,但是中国的稿费一直比较低,在日本,靠稿费来生活现实吗?这样的写作您不急不躁持续了20多年,您写作的原始动力是什么?
李长声:写作完全是出于兴趣,是个人爱好,而且是业余爱好。其实,我算不上中国意义上的作家。在日本,我每年要报税,填写职业,我需要填“文笔业”或“著述业”。上世纪大概鲁迅们的时代是可以的,但80年代以来去日本的人都不可能靠中国的稿费在日本过日子。也许人民币越来越值钱,现在可以了吧,但是我寡作而且不畅销,完全不可能,那就喝不上酒了。我不用日文写作,也不是靠日本的稿费生活。日本作家可以靠稿费过活的少之又少,一些作家到大学当教授,或者到处讲演,就因为光靠那点稿费度日维艰,需要搞副业。我养家糊口的行当是翻译,写作乃业余,所以能不急不躁,估计还能持续下去。想写才写,若不是自己想写能写的,媒体约稿也不应。中国读者把我看成作家,说老实话,我挺不好意思的,但为了卖书,只好跟媒体“狼狈为奸”。我自称随笔家,因为在读者心目中档次好像比作家低。出一本书或好几本书,未必就算得上作家,如今作家的门槛太低了,甚或没门槛,作家不过是写作者的美称罢了。前几天在手机上看了江苏台拍摄的《自适其适》,采访当代书法艺术大家戴明贤,这位老人家说得非常好,例如多读少写,与其写不高明的文章,不如读高明的书。他说:虽然没什么成就,但一辈子沉浸在自己的喜爱之中,也就其乐无穷。他说这是老来的自我解嘲,但我希望自己的一生能这样就好。
提问:不少评论者注意到,您的写作,延续了五四周作人的文学随笔传统,文化味道,不疾不徐的节奏等等,尽管周作人90年代以来有一个小热点,但范围和时间都有限,这种传统是如何在您的写作中发挥作用的?
李长声:我爱读鲁迅,也爱读周作人。我年轻时读过的全集,除了毛选四卷,那是时代所致,出自私心喜爱读的就只有鲁迅全集。周作人是后来才读的,而且读得很零散。从文体来说,我最喜爱鲁迅,但是不喜爱他的性格,虽然他有那种性格才有那种笔法。像一列火车,我自然而然就上了周作人那条岔道,倘若上了别的岔道,或许我的写作会翻车也说不定。我没赶上周作人热,您说的发挥传统也不是有意的。读就是了,喜爱就读得多,所谓近墨者黑,写得也有点像,可能归根结底还在于性格比较像。不过,阅读之广,见识之高,我只能望尘莫及。他见识公允,那不是装出来的豁达,而是天生的平和。
提问:在您的文集中,我特别感兴趣的却正在于您偶尔流露出来的私生活。喝酒、旅游、读书,好像是您生活的三大主题?
李长声:我以前开玩笑,说自己喜好红白黑:红颜、白酒、黑字。开玩笑而已,对于我这种人,红颜不现实。女人是花,需要养,或用金钱或用才貌或用感情来施肥,我没有这些肥料。所以您给我归纳的三大主题才现实。或许可以说,做事营生之外,第一个主题是读书,第二是喝酒,至于旅游,我远远算不上热衷,像人家驴友那样。上高中的时候赶上了文革,我是逍遥派,但人家革命派弄出大串联,我也不逍遥了,坐火车一路站到兰州。好像也因此跟兰州结缘,第一本集子就是敦煌文艺出版社给出的。那时候假装革命,跟着冲击省委,后来人家把一大沓材料寄到学校来。这是我文革期间唯一的造反行动,也是我旅游之始,但可能上了年纪,后来就不喜欢到处跑了。一位我崇敬的作家对日本感兴趣,经常去日本,游的地方比我多得多,使我都愧在日本了。我只去自己喜欢的地方,看看风景,泡泡温泉,然后就喝酒,喝到不知道今宵酒醒何处。您觉得我写旅游有点多,那是因为在日本住了将近三十年,而且是小日本,爱游不游也差不多游遍了。

提问:在日本,用日语生活,用中文写作,这种语言的转换到底意味着什么?是生活还是写作,更能接近自我?
李长声:常看见作家被问为什么而写,倘若有人来问我,我的回答是为自己,为读者,也就是所谓粉丝。我没有更大的更了不起的理由,我从来不关心国家大事。为自己,我只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为读者,我认认真真写。我觉得,用日语生活,用中文写作,丝毫不冲突,反而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促动思考,有意无意地进行中日比较。很多人在日本用中文写作,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到哪里都很文化,往那里一站就弘扬中华文化,所以日本办有很多中文报纸,提供了所谓园地或用武之地;二是写作的人是要诉说自己的遭遇与心情,当然不会说给近乎无关的日本人听,而是要说给自己人,他们才能理解自己,同情自己。日本有女性写作的传统,这可以从历史找原因,而在日本的中国女性写作,无非想诉说,她们远远比男人更想说自己。所以,写作更能接近自我吧。中国有敬惜字纸的传统观念,一旦拿起笔来就像换了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也就未必真实了。
提问:在您的写作中,很少提到出国以前的生活,倒是在写一些美食中(《吃鱼歌》),您好像提到过母亲做的酱豆?和父亲喝酒?这些早年经验,在您的写作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李长声:我要写的是日本,我叫作“贩日”,就像个倒爷。我妈说我一条道跑到黑,我作文也是一条线,不愿意旁骛,即所谓展开,人家的文章是枝丫如盖,我的是一根竹竿。譬如写生鱼片,我吃它并非始于日本,当年在故乡就吃过,当兵时常用来下酒,但我要贩卖日本,也就懒得说。有时也难免不触及自己的生活经验,特别是吃食之类,譬如在国内生活吃生鱼片可能是日本人留下的吃法。我的人生经历很简单,那就是跟祖国一起成长,文革、下乡、当兵、回城,大家挨饿我挨饿,大家出国我出国,如今大家得糖尿病,我也跟着得,一辈子随波逐流而已,实在没什么可写的。但是可以说,我对日本的感受、认识,基本以自己出国以前的生活和学识为背景,那时候的我闪烁在字里行间,也就高不到哪里。

提问:在日本,国家虽小,也更现代,但是很多作家好像有浓厚的故乡情结。您好像经常去参观作家的故居,看他们的文库,写他们在故乡的故事。故乡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李长声:写故乡无非写自己熟悉的事物,写一种经验罢了。大江健三郎在东京写作,写的作品走向世界,但他的文学故乡、文学灵魂是他出生的四国森林。但是像坂口安吾那样的无赖派作家,给故乡题词,题了一句故乡没啥可说的。从地方到中央,还有一个语言问题。譬如村上春树从神户到东京,他说自己使用标准语就像是在用外语写作。一个人如果用外语写作,倘若写得磕磕绊绊,那么,在这个犹如一边学习语言一边写作的过程中,他就会修改自己的真实的体验与感受。村上春树翻译美国小说很有名,但他从来不用英语写作,对所谓双语写作也不以为然。当过日本笔会会长的井上厦从地方来到东京,为自己的方言自卑。当然,这是地方人进入中央环境的心态问题,不是否定方言。好像日本作家常常有一种自卑感,例如夏目漱石,不大像中国作家那样居高临下看读者,看自己笔下的人物。常说日本文化带有哀愁,或许这种哀愁也出于自卑感,这种自卑感自有可怕之处,像三岛由纪夫笔下和尚的自卑,干脆把金阁寺的美烧掉。
提问:您很少直接写自己的故乡。故乡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李长声:我好像对故乡不那么热爱,没有那种像是一种境界的“乡愁”。对故乡的感情也有陈旧的一面,与羁旅、烽火相关,或者父母在不远游什么的。故乡与他乡还有个距离问题,但今天有网络,瞬息万里,有飞机高铁,风驰电掣。我父母健在的时候,我是回来看他们,不大有回乡的概念。别人听我的口音,问起来,我才想到乡音无改鬓毛衰,自嘲是苞米碴子味儿,就像说大连人说话是海蛎子味儿。我贪杯,人家打听了我的籍贯,说一句怪不得。也就这么点故乡的骄傲。近年到过一些地方做活动,却不曾被故乡“召唤”过。
提问:你的写作,写日本,同时心中也有一个中国,写中国,心中又装着日本。您的视角,似乎处于中日之间,而没有落实在任一方。您在写作中有没有“异乡人”的感觉,在,却又不属于任何一方?
李长声:不,我属于中国。我是30多岁来日本的,从语言到思维早就顺拐了,怎么也“归化”不了日本。居处易改,本性难移。所谓异乡人,我顶多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受,不是文学层次、思想层次的异乡人。我写日本,并不把它装在心里,基本是旁观者,而且既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是袖手旁观。对于中国,因为隔了海,也不免作壁上观。就我以及我周围的作者来看,好像作文时基本不选边站。这样一来,也有点难讨好,里外不是人。譬如日本有个财团一拨一拨地招待中国作家、媒体去日本,吃喝玩乐几天,他们回来就大讲日本的好话,但不把我们这些长年侨居日本的所谓旅日作家看在眼里。中国对海外媒体下功夫,如今他们大都召之即来了,但好像不大把旅日作家们放在心上,这倒是符合公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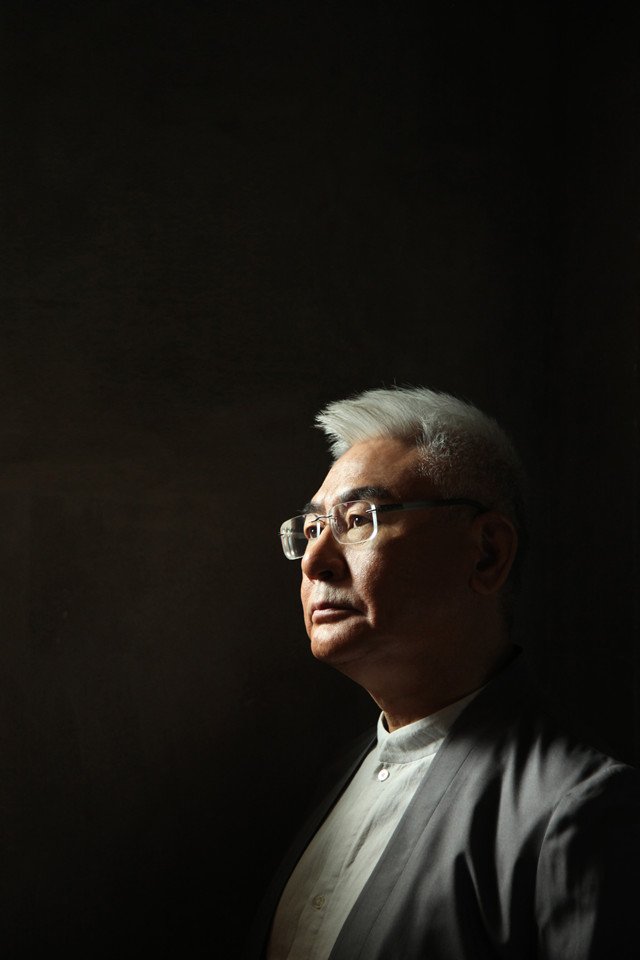
(场地提供:单向空间·花家地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