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新共和》上发文评论安格斯·迪顿的《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书评中,她以对一位大经济学家著作的期待来要求迪顿,从标题、开篇、历史书写、概念描述和论证展开等多个方面给迪顿提意见,希望他能把书写得更加详尽周全。本刊选译部分章节如下。
1.
“如今的生活大概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好。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富裕,而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越来越少。”迪顿在《逃离不平等》的开篇写道。但他马上又说,“然而,数以百万计的人仍然生活在对赤贫和过早死亡的恐惧中。世界是非常不平等的。”在这里“逃离”有双重含义:一是“逃离”过早死亡的命运,一是“逃离”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持续的不平等。
迪顿的书以他自己的感人故事开头。迪顿的父亲,从约克郡矿村的悲惨生活中“逃离”了出来。虽然因为身在矿村未能受到更多的教育,但是他父亲抓住了二战时服兵役的机会,上了夜校,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民用工程师。这位父亲决意并努力让他的孩子受到第一流的教育。现在,迪顿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的两个孩子也上了普林斯顿——这所在迪顿看来要比剑桥在深度、机会、教学方面都遥遥领先的好大学。这就是迪顿一家人前赴后继的奋斗史。
迪顿说,他父亲的故事就体现了《逃离不平等》一书的主题。但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个故事没有讲到任何健康和卫生条件的改变,这才是这本书真正的主题。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关于个人奋斗的经典故事(其中稍许获得军队的帮助),一点都没谈到政府在其中的作用,而这是迪顿认为的,“逃离”大任的担负者所在。实际上,那些通过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机构靠不住,并且认为贫困是懒惰和愚蠢造成的。迪顿知道得更多,他的整本书都在表达,各类机构和政府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希望他能抵挡住用这样一个故事开篇的诱惑,它多少显得有点离题了。我还希望他能稍微打磨一下这个大标题,这让人想到1963年的电影《大逃亡》,写同盟国战俘逃离了纳粹德国的战俘营。把营养不良、传染病同第三帝国作比,是很诡异的,会让人给人类行为中最糟糕的那部分开脱。即便迪顿最终将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因果关系归咎于许多人类行为,如医学发现、政府作为和不作为,将这些本意良好、结果复杂的行为同希特勒的暴行作比,也是不合适的。
虽然一开始几步踏得有点不对,迪顿接下来还是领着读者一起来看人类历史中(尤其近年来)“进步与不平等的无休止共舞”,他的导览自信稳健、引人入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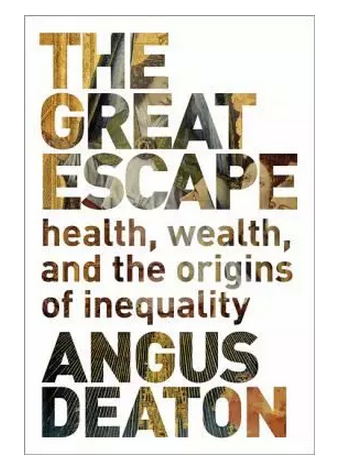
2
《逃离不平等》对于人类福祉的概念并未详作分析,对那些相互竞争的福祉和发展理念,也未加深入辨析。但如果读者耐心搜寻迪顿的观点,还是可以从书中发现很多,包括他对许多他所不认同的概念的有力反驳。
基本上,迪顿的观点是,人类福祉,或者说理想的人类生活,由许多部分组成,每一个就其自身来说都是有价值的。好的生活远不止于财富:它包括健康、教育、远离歧视和压迫(包括“不成为他人追寻财富时的牺牲品”!),以及在一个基于平等原则的民主社会里的参与能力。但是这样的成分罗列有失简单,因为这些成分本身又都包含很多意义。例如,健康就有很多面,包括肉体的活力、良好的认知能力,以及预期寿命。迪顿认为,福祉的衡量是以道德判断为基础的,即便是健康这样人们以为一目了然的领域。例如,要延长预期寿命,就必须优先解决婴幼儿存活率的问题。
因此,迪顿反复猛烈地批评人均GDP足以衡量人类福祉的观点,而这是发展理论中的一大标准,而且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印度首相穆迪,在古吉拉特邦竞选时就提到他在发展方面的成就,但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古吉拉特邦固然在人均GDP上进展不错,但在健康和教育上远没有喀拉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做得好,部分原因就是这两个邦的政府服务质量非常高,而穆迪是反对强政府的。)即便人均GDP作为单一指数来讲已是衡量福祉的最佳选择——迪顿否认这一点,否认的理由也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个论点,即外资的利润往往被投资国拿回去了,因此关于被投资国的人们到底过得怎么样,他们的平均家庭收入会告诉我们更多——实际上,没有一个单一指数真的够好,好到足作表征,因为人类的生命是如此复杂,何为生命中的价值所在,也饱含复杂性。此外,人均GDP没有包含人们在家完成的工作(这一点是南希·福尔布[Nancy Folbre]和其他女性主义经济学家一直强调的,如今已进入研究主流),也没有包含闲暇的价值。虽然在GDP和迪顿提到的其他一些好东西之间,确有一些泛泛的关联,但是这一关联是会被打破的。例如,美国的高人均GDP,并没有告诉我们很大一部分绝望的美国公民体会到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出现在各个领域,如不良的卫生条件,质量低下的教育,无法在政治上发声。
还有一种重又流行起来的观点是,人类福祉可以用“幸福”这种一瞬间的感觉来衡量,这看上去很诱人,但迪顿并没有人云亦云。感觉这种东西当然很重要,迪顿说,但其在标识人们到底过得怎样这方面并不可靠,因为人们会逐渐适应艰苦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这会让他们对自己能达成什么目标做出调整,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适应性偏好”。此外,迪顿说,某些值得追求的目标,如爱和公正,会要求冒险和巨大的努力,同时还可能伴随着痛苦。因此他总结说,幸福,只是“对总体福祉的一个不足衡量”。他明智地指出,我们会更喜欢看“你如何评估你的人生”这样的调查,至少会引发人们思考他们人生的更多方面。迪顿说,这里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对于福祉这样复杂的概念,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衡量标准。
这是本书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虽然其实根本没有独立成章:我是从散落在书中的多个论述里,提炼的这些观点。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分析还是针对健康和收入,福祉的其他方面,如教育和政治参与,虽然屡被提及,但从未被分析。迪顿的主要关切是研究收入和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余的部分则好像铅笔随便涂了几笔,等着别人来完成。
3
在他书中铁定最有争议的一章里,迪顿指出,全球贫困问题不会得到解决,而且事实上,因为过度的外国援助和国际私人慈善事业,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富国的人想要有所帮助,他们从道义上觉得应该出手。但是他们给穷国的那些钱,通常都无助于解决问题。正如经济学家彼得·鲍尔(Peter Bauer)很早就指出的,如果除了资金外,其他所有发展条件都满足,那么资金很快就会从本地产生,或由海外借贷给政府或民间企业。如果其他前提条件不存在,那么资金的流入将是非生产性的且无效的。
对于鲍尔的基本观点,迪顿加上了出于他自己长期经验的更多具体论述。首先,外国援助极少以接受者的实际需要为导向:而更通常地,是由捐赠国的优势群体和利益群体来主导方向。第二,援助通常都是发给政府,而这些政府基本上对于帮助本国人民毫无兴趣。这些钱只会巩固独裁者的权力。即便援助的分发配置并没有什么错误,它也只是顶去了受援国当年政府预算中原本就用来解决这一问题的部分,而把多出来的钱用在其他事情上。更糟糕的是,这通常会降低政府自己解决问题的动力。援助最起码应该是有条件的,也就是根据情况改善与否来判断,但在实际操作中,根本没有任何强制条件,这意味着我们实际上无法研究援助的效果究竟怎样。即便精心设计的援助政策也往往会弱化受援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而这种互信在迪顿看来,是经济与社会长足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点。如果一个政府不经其人民的许可就能筹得资金,机构制度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受人民控制,最终会变得“有害”。迪顿表面上狠心建议停止援助,实际上是因为他在政府及其对人民需求的回应这一问题上,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那么,是否有什么援助能免于迪顿的责难?迪顿说,当一地的人出现大量死亡,急需出于道义援助时,有一些卫生援助可以不受或少受他的批评。他区分了“纵向计划”,即针对某单一疾病的计划,和“横向计划”,即提供广大的健康卫生设施的计划。他认为后者是错误的干预,因为创建卫生基础设施要取得长期的成功,只有通过当地政府才能办到,而当地政府很可能会受到外国援助的负面影响。而前者,相比之下就是外国援助通常有效的地方——针对肺结核、疟疾、艾滋病或其他一些疾病的计划。
迪顿勉强认可说,“横向计划”对那些推行造福人民政策且有记录可循的政府,可能也是个好主意。但他仍持怀疑态度,虽然缺乏证据,他觉得这样的计划至多也只能小有帮助。
读到这里,读者可能会很不安。迪顿正在告诉那些感到内疚、特别想做些什么的人们,其实他们什么也做不了。更糟糕的是,一旦你想努力做善事,其实是把事情往更坏的方向推。这些读者应该读一读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相反观点,以及其他一些充分论证了反对意见的作者。但我希望迪顿能对“纵向援助”的其他一些类型做更多研究。那些世界各地、种类繁多的教育援助进展如何呢?没有一个广大的识字人口,当然不会得到什么好的治理。如果当地政府没法提供教育,那么也许用不那么理想化的手段来实现提升识字率这一目标,还是值得的;而不是让整整一代人在没人干预他们政府行为的环境中长大。

Martha Nussba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