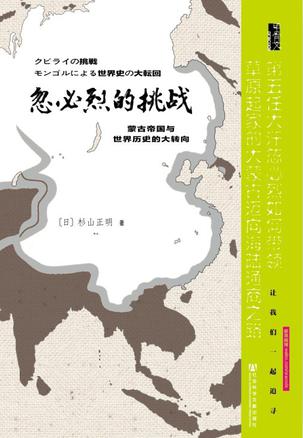
《忽必烈的挑战》
(日)衫山正名
周俊宇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白银资本》和《大分流》这样极具颠覆性的著作产生之后,无论读到何种强调东方世界作用的文字都不应该觉得惊奇。这类作品告诉我们,我们曾拥有比欧洲世界更多的财富,也曾拥有足以和西欧相抗衡的经济实力,只是在1800年之后才逐渐和他们拉开差距。为此,我们曾将近代的磨难归咎于乾隆的短视,也曾埋怨“西方的强盗行径”,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告诉我们,事实远不是我们所以为的那样简单而富有悲剧意味。因此,黄仁宇会将近代问题归因于中国传统中“数目字管理”的缺乏,黄宗智则将关注点放在农民的生计上。他们也许都未曾想过,假如现代历史不是以我们所知的那样出现,一切又将怎样?
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那里,一个由大航海时代开启闸门的、以西欧为中心的生产与流通体系的建立,是现代的基本特征,也是世界成为一体的基础。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则针对此观点,认为忽必烈建立的元帝国已经率先建立了一个世界体系,将欧亚大陆为中心的广大地域组织成了一个经贸的整体。他在《忽必烈的挑战》中就元帝国的产生及其对世界性通商的影响展开了论述。作为该书的核心论题,他从都城营建、征服南宋、海上称雄、商路建设、商业管理、货币改革等方面试图论证以元朝为中心的世界商贸体系的存在。当我们还在争论元朝究竟是北族政权还是中原政权的时候,他的眼界已经超越了“华夷之辨”这个层次,开始关注世界史领域中的蒙古历史,这正是《忽必烈的挑战》最大的价值所在。
这个蒙古世界体系为何能够产生?杉山氏认为,直接的原因就是忽必烈巩固汗位的需要。在他的解释里,忽必烈在汗位之争中完全是篡权者的形象,为了获得各汗国的认可,他需要像以前的蒙古大汗一样,不断地为他们提供财富。最终,他建立了一个以“首都圈”为核心,横跨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大帝国,将蒙古的军事力量、中原的农业经济和穆斯林的商业文明结合起来,让蒙古在世界历史上从征服者转型为统治者与经营者。可以说,杉山所说的具体史实,我们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但我们运用这些事实去搭建的解释系统则与他截然不同。仅就军事、经济与商业的结合而言,有时被归纳为元朝迅速走向腐化的原因,有时被概括为“内北国而外中国”,而忽必烈开创的“两京制”,也被解读为“草原本位”或“草原中心”。杉山则将这些事实与汗位争夺战联系起来,为我们描绘出一个世界体系的雏形。
以往我们说到元明时代中国对“世界”的作用时,常挂在嘴边的是马可·波罗的游记和郑和的航海旅程,但对二者的意义则很难做太多的阐发,因为看上去它们和后来的世界并无太多关系。杉山氏则告诉我们,这两个案例都只是忽必烈所搭建的世界体系中的产物,是这个体系下的细节。这样一来,我们的世界形象一下子伟岸起来——尽管杉山同时也提到,元帝国并不是一个“中华王朝”。
有关元朝是否具有中国属性这一问题,历来就存在争论。而在明初编纂的《元史》中,忽必烈的即位诏书完全是中原皇帝的做派,而且忽必烈本人对汉地文化与制度的兴趣也是读史者所习知的。以往由于文化本位观的影响,常有将元朝摒弃于中国历史之外的观点出现,但元帝国所具有的浓厚的中原气息总是不可否认的。站在汉文化传统的立场上,我们可以说元朝存在“汉化迟滞”的现象,而若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融的角度去观察,我们也可以说,日渐增强的中原色彩,让元朝原本鲜明的征服王朝特征逐渐褪去。
王朝属性问题,对世界体系的有无并不存在支持或否定作用,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于,如果真的在忽必烈个人的政治需求下建立了一个以蒙古为主导、以元帝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那么为什么忽必烈采用如此复杂的方式,而不是更为简便的其他手段来供给各汗国财富,比如掠夺战争或高额征税?杉山笔下的忽必烈,更像是现代经济学家笔下的理性经济个体,一个指挥全局的总设计师,而非一个马背上的皇帝。他和他身边的“策士”们居然能够动用各种手段,比如杉山所强调的蒙古铁骑、汉地物产与穆斯林商团,并大费周章地利用运河、开辟海航、改革币制,以求在商路所及之处获得财富,并维持元帝国在这个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未免有点不可思议。即便是最精明的阿拉伯商人,也不可能提出这样一整套的政策性与制度性方案,说得极端一些,即便是现代中国,通过一代人的努力建立一个如杉山所说的世界体系——哪怕只是第三世界范围内的——也不可能,何况是忽必烈?
另外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忽必烈因为个人原因建立了一个世界体系,那么在以后的元朝皇帝那里,令它能够维持下去的动力又是什么?在前现代的王朝中,决定一种与政权关系密切的事物是否能够存在的,更多时候是政策,以及政策制定者的态度,而非一个并不存在的、能够自己运行的制度。元朝皇帝的更换频率极快,除了忽必烈和末代皇帝元顺帝,其他人在位时间少则一年、多则十几年,且政争不断、政策变动频繁,所谓的世界体系如果真的存在,其持续存在的政策性或曰政治性原因在哪里?杉山将蒙古世界体系的崩坏起始时间定在一三三零年代,认为蒙古帝国联合体从这时开始瓦解,而对元朝内部的皇位更替与政策变化所能产生的影响则未置一词。
在另一个地方,杉山强调了元帝国死刑判决数量极少的情况,似乎将之作为可赞扬的事情,而这种政策性现象,正是学者们将元朝看做“罪犯天堂”的重要论据:伴随着低死刑率的,并不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而是高犯罪率。这种有些天真的误解,不知是否和忽视元朝政治动态有关。
在对蒙古的世界体系进行评估时,杉山有将这一“世界体系”产生的影响放大的做法。他以“大明可汗”为论据,认为这就是世界体系的残留影响。不过,在邦交方面,沿用前朝旧称稍加改作的形式,在新王朝建立之初时往往会出现,而且即便这称号被长期使用,比如唐代的“天可汗”,所体现的也只是中原皇帝在宗藩关系上的主导身份——周边各邦共同拥戴的“可汗”,而非某个跨国体系的主导者。
另外一个将“世界体系”作用放大的例子是对明成祖朱棣的评价。杉山认为明成祖迁都北京、对北元进行征伐之举就是想要“重现大元汗国”。明成祖迁都与北伐的目的,吴晗就曾做过研究,其他学者也有过相关论述,其目的应该不是重现元帝国,而是尽可能地消灭元朝的残余势力。杉山又以明成祖的身世传说为例,认为人们传说他是元顺帝之子并非没有原因,正是因为他想要建立元朝那样的大帝国才会如此。如果我们注意另一个有趣的传说就会发现,这个观点实难成立。在传说中,元顺帝并非蒙古后裔,而是宋恭帝的私生子,这和秦始皇的身世传说有些类似,目的都在于否定其继位的合法性并贬低其出身。而明成祖的身世问题与此相类似,但一定程度上是与其伪造身世、令后人遐想有关。
既然所谓蒙古的世界体系是否存在非常令人生疑,其阅读意义又在哪里?在我看来,这是东亚学者在欧美学术范式下对其自身历史的审视和对现代起源的解释。
现代世界究竟为何出现,以怎样的形式出现,是很多西方学者探讨的论题。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沃勒斯坦等都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现代世界产生的原因。对这些理论,东亚学者也日渐在反思中进行回应,比如余英时就以《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来回应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同样,杉山氏也以《忽必烈的挑战》来回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余英时通过研究中国宗教与儒家观念在中唐以后的世俗转向,对所谓“商人伦理”进行了剖析,使用韦伯的基本理论对中国前现代社会晚期的历史进行考察。杉山在研究取向上和余英时极为相近,使用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基本界定,从东亚世界寻找与这一学说相契合的因素,再以此对沃勒斯坦的观点进行反击,正是所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他们的研究都没有方法论的创见,只有将东亚事例与西方理论结合的试验。这种试验本身并不成功,而且都有将案例抽象化和误读的表现,但他们也通过这种试验证明了一个问题:在明显从欧洲经验出发,对现代性进行解释的理论下,试图以东亚历史去迎合这些理论的工作本身也是对欧洲经验的一种默认,且只能使对东亚历史的解释落入欧洲中心的陷阱。现代国家从欧洲出现,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且是一种偶发性现象。偶发性就意味着欧洲出现现代化进程时东亚世界并未出现类似的反应。如果一定要在并未发生的历史中寻求欧洲经验,无异于缘木求鱼。
更重要的是,用东亚历史去做欧洲经验的注脚,会抹杀东亚历史本身存在的特征。就以《忽必烈的挑战》为例,沃勒斯坦所提出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是以西欧经济发展为前提,以海外开拓为动力,以形成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与现代帝国为结果的,而在杉山的论述中,忽必烈之所以能够建立一个蒙古的世界体系,则是以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汗国为基础,以元帝国的各项措施为手段建立起来的,一个强大的前现代帝国的出现不是结果而是前提,政策性因素也成为非常重要的支撑,这和沃勒斯坦的理论模型本身就存在差异,而杉山本人对此似乎并未特别注意,而是将笔墨更多放在描述蒙古世界体系的辉煌这一点上。也许,重视元帝国本身的特性,重视元帝国、阿拉伯世界及欧亚其他地区在商贸交往上的复杂关系,会发现一个真正的前现代体系,如果它真的曾经存在过。这样,我们就可以给《白银资本》和《大分流》写一个“前传”,探讨大分流时代到来之前的东亚世界。
